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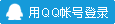
x
[ 本帖最后由 purdoo 于 2016-4-27 09:27 编辑 ]\n\n医学院的第四年,我观察到,相继地,班级里许多的同学选择了没有那么艰辛的专科(放射科或者皮肤科,比如),然后申请住院医。十分不解,我收集了几所精英医学院的数据,然后看到了相同的趋势:临近医学院终结,大部分学生会倾向于那些“生活方式相关”的专科——工作时间更人性化、工资更高、压力更小——医学院申请文章中的理想主义褪色,或者遗失了。毕业临近,我们坐下来,根据耶鲁的传统,重新书写我们的毕业宣言——一篇混合了希波克拉底、迈蒙尼斯、奥斯勒以及其他几位医学先贤的词句——几个学生争论要不要移除关于坚持把患者的利益置于我们医生利益之上的词句。(我们其余的人没有让这种讨论持续太久。词句留了下来。这种与医学精神相悖的自我主义震动了我,应该被记下来,完全合理。实际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这样选择工作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但这恰恰是重点。将生活方式——而非召唤放在首位,是找工作的方式。)
$ F O7 e# S! H5 @( b
5 x/ b$ f8 b9 i; ], |0 a" ]% h至于我,则会选择神经外科作为自己的专科。这个选择,我已经发反复思考了很久,在一天晚上被巩固,那是在手术室旁边的房间,我默默地带着敬畏,听着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和一对父母坐下来,他们的孩子生了巨大的脑瘤,当晚入院,抱怨头痛。他不仅仅陈述了医学事实,而且顾及了人性的因素,认同悲剧的局面并提供了指导。然而,孩子的母亲是一个放射科医师。肿瘤看上去是恶性的——妈妈已经研究了扫描图像,如今坐在荧光灯下的一把塑料椅子上,神情灰败。) Q* ?2 `- c- ~: e. D' F
4 l1 y( g" O9 P8 c1 d$ r8 }* L“好吧,克莱尔,”医生轻声地开始说道。
/ v6 {" K- r& o& G$ e; m+ Q/ C( o" p- v# s, {$ d1 ^5 @: j
“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糟糕么?”妈妈插话,“你觉得是癌症么?”
: J) B; Q n1 w( q& f& X6 e5 [1 ~% }( O0 ^0 E9 h' S/ q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相信你也知道——你的生活即将,甚至已经改变了。这会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明白么?你们必须互相支持,但是必要时你们也必须要休息。这种病要么会让你们相濡以沫,要么会让你们分道扬镳。你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相互支持。我不希望你俩整晚不睡陪在床边,寸步不离医院。好么?”
: h; J, _' ^. e4 @
+ O, g- r" g9 D9 t: k8 C$ x他继续描述手术的计划,可能的成果和可能的后果,有什么需要马上决定,什么需要开始考虑但不必立即决定,还有什么样的决定是他们目前还不必担心的。谈话结束,这一家人并没有轻松起来,但是看上去已经能够直面未来了。我看着父母的脸——最开始灰暗,呆滞,简直神情恍惚——而今打起了精神,集中注意力。坐在那里,我意识到,交织了生、死和意义的问题,人们都会在某一时刻碰到的问题,通常会出现在医学场景里。某个人遭遇这些问题的现实场景中,它变成了一种必然的哲学和生物学操练。人是有机体,受制于物理规律,包括,唉,那个声称熵总是递减的定律。疾病是分子的行为不端;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则是它的终止。 k+ q7 o7 M' x+ k- j6 f/ ?8 F. z
) |/ r" ` _5 G+ F
所有的医生都治疗疾病,神经外科医生则在认知的熔炉中周旋:所有的大脑手术,不可避免都是我们对自身物质的人为操作,任何与经历脑部手术病人的对话都会遭遇这一事实,别无他法。此外,对于患者和家庭,脑部手术通常是他们经历过最具戏剧性的事情,其本身,对任何主要生命事件都具有影响。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问题并不简单的是生与死,而是什么样的生活值得去过。你愿意用你的,或者你母亲的讲话的能力,去换取不能讲话的多活的几个月么?愿意用视觉盲点的扩大,去换取致命脑出血微小可能的消除么?用右手功能换取癫痫的停止?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经历多少神经痛苦才会说死亡反而好些?因为大脑调停着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任何神经外科学问题都强迫患者及其家人——最好有医生指引——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会让生命足够有意义,值得继续生活?
' [4 [/ B& H' W
j {. @+ @' g+ E- y& ~) Z我被神经外科俘虏,被它对于完美不折不扣的召唤所倾倒;就像古希腊“ARETE精益美德”的概念,我觉得,高尚需要道德、情感、精神还有物理上的精益。神经外科似乎呈现着与意义、认识和死亡最具挑战最直接的交锋。伴随着肩负的巨大责任,神经外科医生还是很多领域的专家:神经外科学,重症监护医学,神经学,放射医学。不仅需要训练自己的意识和双手,我懂得;还需要训练自己的眼睛,甚至还有其他器官。有个想法势不可挡,令人神往:也许我,也能加入那些大师的行列:跨进在情感、科学和精神问题最稠密最复杂的领地,并且发现或者发掘到出路。 |
|
|
|
|
|
|
共4条精彩回复,最后回复于 2016-5-11 09:11

尚未签到
医学院毕业之后,卢茜和我新婚不久,到加州开始我们的规培。我在斯坦福,卢茜去了北面不远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正式变成了身后之事——如今真正的责任正等待着我们。不久之后,我就在医院里结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具体而言,有维多利亚,她也是住院医;还有翟复,一个比我们资深几年的普外科医师。在接下来的七年规培里,我们会从医学剧的见证人成长为其中的领衔主演。
/ W/ l, w6 d( r/ \* h6 x, F
7 O5 `4 `7 P5 s8 @8 J( G6 t住院医的第一年,作为实习生,有点更像是生与死背景下的小文员。然而,即便如此,那时候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医院的第一天,主任医师跟我说,“神经外科住院医不仅仅是最好的外科医师——我们是整个医院最好的医师。那是你的目标。让我们为你自豪吧。”;科主任,经过病房:“要一直用你的左手吃饭。你必须学会左右开弓”;一个资深住院医:“提醒一下——主任正在闹离婚,所以他现在真的把自己扔进工作里了。别和他闲聊天。”即将离开的那个实习生,本应该指导我的,却只是交给了我一个四十三个病人的名单:“唯一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总是能把你伤的更深,而你不能叫暂停。”然后就走开了。) V0 o& X" `3 L% z/ I& o
# F9 Y* o3 N% l" j6 F+ F
最开始的两天,我都没离开医院,但是不久之后,那些似乎做不完的,需要耗费整天时间的文牍工作,变成了不过是一小时的活儿。然而,当你在医院里工作,你填写的表格不仅仅是表格:那是风险和胜利的片段。比如,一个八岁的男孩,曼休,,有天抱怨头痛入院,结果却得知他的下丘脑附近长了一个肿瘤。下丘脑规制着我们基本的内驱:睡眠,饥饿,渴,性。任何肿瘤残留,都会让曼休的生活变成一个放射治疗、后续手术和脑导管的受害者……简短而言,会吞噬他的整个童年。彻底的切除会避免这些,但是可能会有伤害到下丘脑的风险,那会让他成为食欲的奴隶。外科医师只能从曼休的鼻腔深入一个内窥镜,钻开他的颅底。到了里面,就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平面,摘除了肿瘤。几天之后,曼休就在病房里活蹦乱跳,从护士那里顺糖果吃,准备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开心地填好了他出院的无数张表格。
5 `" W' H# E2 ?
: @& G* a- P( T. E5 N( j5 i: w我在某个周二失去了第一位病人。
% ~9 W, u9 J. U4 t
. W$ W0 U! ?/ l4 A u6 a$ A一位八十四岁的老妇,瘦小整洁,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在那里我当了一个月的实习生。(解剖时,病理学家得知她的年龄会大吃一惊:“她的器官年龄也就五十岁!”)她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的便秘而入院。在希望她的梗阻能自行化解的六天之后,我们做了个小手术来助其实现。星期一晚上八点,查房时我见到她,她很清醒,没什么事。聊着天,我从口袋里掏出当天的工作清单,划去了最后一项(术后检查,哈维太太)。该回家休息了。
$ M* h. F# ~" G& C! P* H
3 ~ ]* r4 E0 N$ M) V午夜之后,电话响了。病人垂危。带着突然摆脱繁冗的事务性工作的沾沾自喜,我从床上坐起来,吐出一连串的命令:“一升大剂量LR,心电图,胸透,STAT ——我正赶过来。”我给主治医打电话,她让我加上病理化验,掌握更多情况之后再给她打电话。我冲到医院,看到哈维太太正挣扎着呼吸,心跳过速,血压骤降。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她都没有好转;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值班的普外医师,我的呼机不断鸣叫,有些是我可以不管的(病人需要安眠药片),有些事不能不管的(急诊室里有一例大动脉动脉瘤断裂)。我像是淹进水里,被四面八方拉扯着,而哈维太太还是没有好转。我安排了转到ICU重症监护室,那里我们用药物和液体轰炸,以防她死掉,接下来几个小时,手术室内有一个威胁着要死的病人,ICU里的另一个正在快速死去的病人,我在二者之间疲于奔命。到了5:45,急诊室的病人再去手术室的路上,哈维太太相对稳定了。她需用了十二升液体,两单位血浆,呼吸机,还有三种不同的升压剂维持着生命。4 m$ X _7 z3 E3 c# J
7 h+ F, m% [' S# ?* t
周二晚上五点,当我终于离开医院,哈维太太并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晚上七点,电话响了:哈维太太不行了,ICU正在尝试心肺复苏。我奔回医院,再一次,她挺了过来。差一点儿。这次我没有回家,在医院附近找了点吃的,以防万一。 Y+ x" R4 k- `; b* t
; W+ r% Q) M! G晚上八点,我的电话响了:哈维太太刚刚去世。* ?2 W D* u4 }% B' c* E+ `5 K! ]6 ]
' `) _1 a- J% `& ]
我回家去睡觉。8 s! U6 ^" ?- q2 B! Q* Y
. M O) }3 w) l. Q, s8 }* h' i
我处于一种介于愤怒和悲伤的中间状态。无论如何,哈维太太从一大堆表格中跳出来成为我的患者。第二天,我参加了她的解剖,看着病理师切开遗体,移除器官。我亲自检查,亲手逐一触捡,检查了我在她肠道上系下的结。从那之后,我下定决心,把每一张表格都当成病人看待,而不是反过来。 w* d. t r$ R* ~* B+ X
* ^4 \ w$ d5 W4 H* m
那第一年,我瞥到了死亡之中自己的那部分。有时是我在角落里窥探的时候看到,其余则是人在当场,感觉窘迫。这里是我看着死去的几位:% A0 A: m) j" [4 f
8 |1 r1 W9 U. r2 f; d9 z1.一个酒精成瘾者,他的血液不再凝结,死于关节和皮下的内出血。每一天,淤青都在扩散。神志不清之前,他抬头看着我说,“真不公平——我一直都用水稀释了我的酒。”& |% `2 _/ j$ a O6 f! Y
; h! ?$ O3 N; G0 L/ \( F
2.一位病理师,死于肺炎,在去楼下解剖室之前,死亡前最后的喘鸣——那是她最后一次的病理实验室之旅,而她那里渡过了生命中的许多个年头。5 c+ r/ A' N/ x- ^& `3 W
. m6 ]3 G' h$ V* W3.一个做了神经外科的小手术,来治疗面部被闪电击中穿过导致的疼痛:一小滴液体水泥被放置在可疑的神经上面,以避免血管压迫。一周之后,他头部剧痛。几乎做遍了所有的测试,却没有诊断结果出来。3 q( L- v) p; B) G9 `& c
4 y7 |$ Z w) x$ E# V5 l4.几十例脑部创伤:自杀,枪伤,酒吧斗殴,摩托车祸,车祸,被麋鹿攻击。
/ {2 d" a4 L) p* f6 w5 p9 V$ M5 g4 R5 B8 q& k
有些时刻,它的重量变得简直可以察觉。在空气中,在紧张和悲痛中。通常,你吸入它却注意不到。但是有些日子,比如潮湿的天气,它会有让人窒息的分量。有些日子,我在医院里的感觉是这样的:被困在无边无际的夏日丛林中,汗流浃背,死者家属的泪雨滂沱。 |
|
|
|
|
|
|

尚未签到
住院医师的第二年,危急情况你总是第一个到场。有些病人你回天乏术,有些可以抢救回来:第一次我推着昏迷的病人从急诊室冲进手术室,把他的颅内出血抽出,然后看着他醒过来,开始和家人说话,抱怨头上的切口,在欢欣的眩晕中我迷失了方向,凌晨两点钟走在医院里,终于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花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我才找到出路。
; d2 K" h0 Z% g3 b2 m7 B0 U, ^
; a7 p6 Y6 i5 ?, c0 U- k, D工作时间表需要你付出代价。作为住院医,每周工作时间长达一百个小时;尽管官方规定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封顶在八十八小时,然而却总有没完成的工作要做。我眼睛流泪,头昏脑涨,凌晨两点还要喝下功能饮料。上班时,还能勉强挣扎着坚持,而一走出医院,那种极度疲劳就会击中我。踉踉跄跄穿过停车场,我通常需要在车里睡一小会儿,才能开车十五分钟到家睡觉。# |" G g# A& Q/ K$ b, E8 O2 }
% X! S5 x3 F* l
不是所有的住院医都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有些人就是没办法接受批评或责任。那是一位天分很高的外科医师,却不能承认他犯的错误。有一天我和他坐在休息室里——因为他求我帮忙挽救他的职业生涯。. E! g1 v0 A( \ o7 g
* V4 |. [) _+ G* b“你需要做的,”我说,“不过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很抱歉。那是我的错,我不会再让它发生了。’”
% Z" ] J) w, t: n$ _+ R# a5 E
' T! u- M m- c4 F F6 O. `. l* I _9 I( I“但那是那个护士——”
' D7 v I4 f" O; V2 l L- X1 g$ j1 B) y& v# `
“不行。你必须要发自内心的说出来。再试一次。”
$ ?8 v# G7 S+ t* g4 b, }1 m' H( W9 z" m
“但是——”$ Q. G' t, x+ O9 l/ P% s/ ?
/ b8 t+ v. A c* j: G2 D! q2 j3 Q“不行,说出来吧。”
" \1 v( V, L9 Q9 j$ O# ~4 X1 L* y( a# u: t! P1 x
如此这般翻来覆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我知道,他毁了。. P, O; S8 s4 V5 D" R! e5 j' z. u
% ]9 _# m1 Z Z压力把另外一个住院医完全驱逐出了这个领域;她选择了离开,去做一份没这么艰苦的咨询工作。
) G q+ H F9 n7 a. ^- k) z/ ]
5 a; p! m5 _ T1 d( `0 [ {) }还有人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 X# W5 {0 V& [6 E1 f2 G5 w# |" N; \' O2 E% I
随着技能增长的,是我的责任。学习着去判断谁的生命可以被拯救,谁的不行,谁不能强求难以达成的预后的能力。我也犯过错。推了一个病人到手术室,抢救过来的大脑让能他的心脏继续跳动,却再不能说话,他通过一条管子进食,整个人报废到一种他自己永远不可能想要的生存状态……我逐渐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比病人死亡更恶劣的失败。无意识新陈代谢的微弱存在,成为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通常会变成一种模式:最终家人们没办法仔细照料,探访渐少,致命的褥疮和肺炎发生。有些人双眼睁开,坚持要这样的生活,并拥抱各种可能。但是很多人不要,或者不能要,神经外科医师必须学会去裁决。) f$ ^9 j$ j7 ` ^8 E1 m" I! W
: D; F1 `+ m+ |7 y
我开始从事这种职业,部分是要追逐死亡:掌握它,揭露它,正面直视它,目不转睛。神经外科学,交织着大脑和意识,也交织着生与死,吸引着我。我曾认为,生活在这两者中间,给我提供的,不仅仅是慈悲行动的舞台,也是自己存在的提升:更远地远离琐碎的物质主义,远离自命不凡的渺小,抵达那里,抵达物质的核心,抵达真正的生与死的决定和挣扎……以期会在那里发现某种超然的存在?
4 h# w8 M1 ~* s- `, R' `0 ]5 x8 ~! W3 ]0 Z
但是在住院医期间,还有另外一些事情逐渐浮出水面。在这种脑部损伤的密集炮火齐射下,我开始怀疑,距离这种时刻的光焰如此之近,只会使我看不到它的本质,就像试图通过直视太阳来学习天文学一样。在病人的关键时刻,我仍然没有真正和他们在一起,只不过是在旁边而已。我观察了很多苦难;更糟糕的是,我开始习惯了。人被淹没,即使是浸在血泊里,也会调整,学习漂浮,学习游泳,甚至学习去享受生活,和护士、医生,还有其他抓住同一条筏子的人一起,被同一个浪头困住。& n) J! n, ?: h! B% Q$ P
2 |: m4 _4 | Q& |% E( c
我的住院医伙伴,翟复,和我都在创伤科工作。他呼我到下面的创伤室,有一例头部创伤并发,我们总是很同步。他查看了腹腔,然后问我对于患者认知能力的诊断。“好吧,他还能做个参议员,”有一次我这样说,“但只能做那种小州的参议员了。”翟复笑了,从那之后,各州的人口成为我们脑损伤严重程度的评估标尺。“怀俄明还是加利福尼亚?”翟复会问,从而决定他的治疗强度。或者我会说,“翟复,我知道他的血压不稳定,但是我得把他弄到手术室去,要不就只能当华盛顿州或者爱达荷州的议员了——你把他的血压稳定了吧?”
% _. x7 }, `) v: V/ B0 j) _& h( _0 J( M3 t2 M- F+ L
有一天,我正在在食堂拿我的经典午餐——健怡可乐和冰淇淋三明治,呼机宣布来了一个重创伤患者。我跑到创伤科,把冰淇淋三明治塞到电脑后面,这时护理人员也到了,推着轮床,陈述病情:“二十二岁,男性,摩托车车祸,时速四十英里,可能脑浆从鼻子里流出来了……”$ D0 v- B, F g* v. h0 |
: e! z2 u# Y; u我直接开始工作,要插管托盘,评估其它生命体征。安全插管之后,我开始检查他各种创伤:面部淤血,硬地擦伤,瞳孔涣散。我们推注了甘露醇来降低大脑水肿,推他做扫描:破碎的颅骨,严重出血弥散。我已经开始在脑海里计划头皮切口,如何钻骨,排出出血。他的血压突然掉下来。我们把他又推回创伤室,就在其他的创伤科成员到齐的时候,他的心脏停了。围绕着他刮起一阵旋风:导管插进了股动脉,管子深深插进胸部,药物推进了静脉,与此同时拳头敲击着心脏来保持血液流动。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只好由他结束死亡之旅。头部伤成那样,我们一致嘀咕着认同,死了反而更好。
0 j# |' P b+ \9 z/ U' L& M" x( B$ O
家人被带进来查看遗体的时候,我溜出了创伤室。之后才想起来:我的健怡可乐,我的冰淇淋三明治……还有创伤室内的闷热。有了一个急救室住院医顶替我,我鬼鬼祟祟又溜回去,在已告不治的死者父亲面前,挽救我的冰淇淋三明治。: S2 {8 D+ ~* C" ~
" Q5 H, i9 w; e: [冰箱里放置三十分钟,三明治复苏了。味道不错,我想,在家人做最后告别时,从牙缝里剔着巧克力碎。我琢磨着,在作为医师不长的时间里,是不是我的道德滑坡要远比提升严重得多。
, @; ]$ x ]! ], x) L/ B/ z# z7 D! {
几天之后,我听说自己一个医学院的朋友,罗蕊,被车撞了,神经外科医师做了手术努力挽救她。她病危,之后复活,之后一天死了。我不想知道更多。那种某人单纯地“死于车祸”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这些字眼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全部的画面会从里面冒出来:轮床的滚动,创伤室地面上的血,通过喉咙插下去的管子,胸腔的敲击。我能看到手,我的手,正剃着罗蕊的头发,手术刀切开的头皮,能听到钻头的啸叫,闻到烧焦的骨头味,骨屑旋飞,还有我撬开她一小块颅骨的开裂声。头发剃掉了一半,脑袋变形。她失败了,没能把自己再重新拼合起来;成为了家人和朋友的陌生人。可能还有胸管,还有一条腿在做牵引……% J, x$ F2 O2 ~9 o& _1 M( _
. [: M. P2 s( i% t. j我没有问细节。我已经有了太多的细节。
# ?/ n, G/ O# E6 p" j$ ?' B
d* g: G6 Y) a" w h! J: h那个时刻,所有失去同理心的那些场景卷土重来:顾不得病人顾虑,催促出院;那些因为其他迫在眉睫的需求,而忽略了病人的疼痛的时刻。那些我见过的受难的病人,书写病历,干净利落归入不同的诊断中的,却忽视了人文关怀的重要,——都回来了,带着仇恨和愤怒,势不可挡。, w, f8 o# O, B4 ^1 J9 g0 A: b+ j
5 g0 T4 [7 N( D7 B0 v, R; m8 O
我害怕自己正落入托尔斯泰笔下的医生的俗套,浑身上下散发着空洞的形式主义,只知道死记硬背的治疗方法——彻底遗忘了人性的重大。(医生们逐一来看她,会诊中主要用法语,德语还有拉丁语交谈,互相指责,为他们熟悉的疾病开出差别巨大的各种药品,但是最简单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他们根本不知道娜塔莎得的是什么病。)有过一位母亲,刚诊断出来脑癌。茫然,恐惧,不知所措。当时我很累,意识游离。我匆忙回答了她的问题,向她保证手术会成功,也安慰自己:确实没有时间回答她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挤出时间来呢?一个很凶的兽医不听劝阻,瞒了医生、护士和理疗师几个星期;结果后背的创口开线——正如我们警告过的。我被从手术室呼叫出来,缝合了他开线的伤口,他痛的大叫,我则告诉自己,这都是他自找的。9 H. I2 F0 Q$ G7 {
; N* z$ @: \. v2 D0 {- Y0 L
没有人是自找的。7 p6 F* ~4 T3 _' f2 C. ~1 |7 C0 C
% O1 ]# k. y" {- E* m
我找到了可怜的慰藉——得知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和理查德·瑟泽坦白,曾做过更糟糕的事情,我发誓要做的更好。在悲剧和挫败之间,我担心自己会视而不见极其重要的人类关系——不是患者和家人之间的,而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技术上的卓越还不够。作为住院医,我最高的理想并非挽救生命——所有人终究都要死——而是引领患者或家人,形成一种对于死亡和疾病的理解。当一个致命的脑部出血病人入院,与神经外科医生的第一次对话,可能会为家人如何回忆他的死亡染上永远的底色:从平静的放手(“可能他的命数到了?”)到开放痛苦的惋惜(“这些医生根本没听!甚至都没有尽力去救他!”)。回天乏术之时,语言是外科医师仅剩的工具。
3 ]+ N8 _" t" m( [1 j0 v
9 Q- y6 ^6 f! D2 k& F' x% g7 B在严重脑损引起的独特苦难之中,痛苦往往更多的是由患者家人承受,而非患者本人。对于整体严重性失察的不只是医师们,就连围绕着被爱者的家属——他们深爱的人头发剃了,里面是损伤的大脑——通常也不能察觉。他们看到了过去,沉淀的记忆,真切感受到的爱,全部被面前的身体代表着。我看到的是可能的未来,通过颈部切口连接的呼吸机,苍白的液体顺着腹部的管子流进去,可能的漫长而痛苦却只能部分恢复的康复过程——或者更多时候,很可能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人 一去不复返。在这种时刻,我通常不会扮演死亡的敌人,而是他们的使者。我只能帮助这些家人理解,他们认识的这个人——完整,活泼独立的人——如今只活在过去了,而且我需要亲友的投入,来理解他或她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轻松死去,还是靠一袋袋的液体进去,其他东西出来,毫无挣扎之力,只能承受。
% p- N- @& u+ R! E. B" {" ~' K' [6 ~% Z! E2 `( F
如果年轻时的我虔诚一些,可能已经当了牧师——因为我追寻的其实正是牧师的角色。 |
|
|
|
|
|
|

尚未签到
9 Y1 t& C1 z8 a/ `随着新的关注重点,《知情同意书》,病人签署一纸文书来授权手术的惯例,已经变得不再是单纯的法律程序——尽量快速列出所有的风险,就像新药广告的画外音——而是一个与苦难同胞缔结盟约的机会:我们与你同在,这是前方的通路——我承诺会指引你,竭尽所能,去往另外一边。
( h; v3 N) K! W2 w8 k
% s: O4 t/ `- v. m8 f住院医生涯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效率更高,经验更加丰富。终于我可以稍微松口气,不再宁愿舍弃自己的小命也不松手。如今我在接受自己患者所有的福祉责任。* b( }! o' d4 h, h1 g6 c; d
& }& y/ y8 X+ M' o, S. R我的想法转向了父亲。作为医学生的我和卢茜,当年曾经在柯英曼参加过他的住院值班,看到他为病人带来舒适和轻松。父亲问一个心血管术后病人:“饿不饿?我能给你叫点什么吃的么?”
- ~4 Y; W! \8 C: R5 S0 `& K
3 m" x6 D5 C1 M4 ]6 \7 [, }& ]“什么都行,”病人说,“我快饿死了。”' w% U8 c. G" s: x" B$ K
t5 B$ x* C) H; N7 [
“好的,龙虾和牛排怎么样?”他拿起电话呼叫护士站。“我的病人需要龙虾和牛排——速度快点!”然后带着微笑转过来对病人说:“马上就来,不过有可能看上去更像个火鸡三明治。”/ j" _1 F: S! o# i
1 ?( M; o5 w* J他和病人形成的轻松关系,为病人徐徐注入的信任,对于我是一种启发。
4 V& e& H3 B7 T9 E! A* F
3 Q6 Z/ P8 e* r% j; B( M5 I' v6 n" r一个三十五岁的女患者坐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她在给妹妹选购生日礼物时癫痫发作。扫描显示,一个良性肿瘤压迫了她的前额叶。至于手术风险,那简直是最好的一种肿瘤,长在最好的地方;手术几乎肯定能够消除她的癫痫。替代方案则是伴随一生的毒性抗癫痫药物治疗。但是我能看出来,毫不夸张,开颅手术的概念把她吓坏了。从喧嚣的购物中心,被送进一个布满奇形怪状的警报器,滴滴作响的设备,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陌生重症监护室,她孤立无援。倘若我事不关己的高谈阔论手术风险和潜在并发症,她很可能会拒绝手术。而我则可以在表格上记录下她拒绝手术,之后存档,认为自己的义务已尽,继续下一个任务。反之,经过她的同意,我叫来她的家属陪她,平静地从头到尾解释了方案。谈话中,我能看出来,她面对的数不清的选项逐渐缩减成一个艰难,却可以理解的抉择。我在一个空间和她相遇,在那里她是一个人,而不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她选择了手术。手术进展顺利。两天后她出院回家,癫痫再没有复发。8 a( f$ d! K( v7 r$ q- n* v
( ^# _; m# C' s2 e5 T任何的重大疾病,都会改变病人——实际上是整个患者家庭的生活。而脑部疾病还有着它独有的额外的奇怪之处。儿子的死亡已然挑衅了父母整个宇宙的秩序;而当病人已经脑死亡,却体温正常,心跳继续的时候,又是多么的让人更加费解呢?“灾难”一词的词源是指一颗星星的碎裂,当病人听到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诊断时,没有什么比从直视患者的眼睛里看到的图像更加有表现力了。有时候消息太过令人震惊,以至于大脑会出现电力不足。这种现象被称为“心源性综合征”,一种人们在听到坏消息之后会经历的严重昏厥。我母亲大学时代,得知她1960年代乡村能给与她上大学的权利的父亲,在漫长的住院治疗之后终于死去的消息,心源性癫痫发作了,一直持续到她回家参加完葬礼。我的一个病人,一诊断出来脑瘤,就昏迷不醒。我开了一系列的病理检查,扫描和心电图,搜寻着诱因,没有结果。决定性的测试却是最简单的:我把病人的胳膊抬到他的面部上方,然后松手。一个处于心源性昏迷的患者,仅残存着避免伤到自己的意识。治疗包括语言安抚,直到你的话语接通,病人醒来。6 g: U9 g7 g) x) _# K& \) M# o
- Z$ M3 E4 k e3 h4 B/ q! R脑癌有两种来源,一是原发脑癌,从大脑中生成,另一种是转移性脑癌,由身体的其他部位转移过来——通常是来自肺部。手术不能根治,却可以延长生命;对大部分人而言,脑癌意味着一年,或许两年内的死亡。李太太年近六十,灰绿色眼睛,两天前从她一百英里以外家附近的医院转到我这里。她丈夫,花格子衬衫扎进清爽的牛仔裤里,站在病床边,不安地摆弄着结婚戒指。我介绍了自己,坐下来,她告诉我,几天前她感觉右手刺痛,之后右手失去控制,直到连衬衫纽扣都系不上了。怕自己中风,她去看了当地急诊,做了核磁共振成像,之后被送到这里。
8 A& z( C" a4 p# ~: P% l
8 q9 s4 z! q4 u6 H6 W' ?/ C“有人跟你讲过核磁共振结果么?”我问。3 H& X( B$ l. d4 y& o: p7 K4 }
4 K7 C W3 }4 d: }; s7 @“没有。”球是被踢过来的,情况艰难时往往会这样。多少次我们和肿瘤医生争论,告知患者到底是谁的工作。我自己不也是这么做了很多次么?好吧,我明白了,就此打住。
2 B6 b% F' C! Y3 Y. D! e
3 {5 D' w) Q% X# O) P“好吧,”我说,“我们要谈的不少。不介意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理解病情的?听一听能有助于我理解,也能确保不会留下没有解答的问题。”5 X9 t3 \% V7 Y9 P) `5 b
; I- R/ v) z- {* X8 G7 o" X3 l! o
“呃……我以为得上的是中风,这么说来……不是?”. ]. O# u0 L; Y7 L! R7 z! O% J
, T" X( R# J) O! y' |, c, b& P
“对的,你得的不是中风。”我顿了一下,能看到她一周前的生活,和即将进入的生活之间的巨大裂隙。她和她的丈夫似乎都没有准备好听到“癌症”二字——谁又能准备好呢?于是我退后了几步。“核磁共振显示你大脑里有个阴影,症状就是那阴影造成的。”
' u N; N$ n' a5 i8 o% _/ c8 a7 d7 o$ ?$ z
一片寂静。- t/ K% W9 K. F3 w4 W- J
: z7 j/ q2 ~( l. x/ W) E4 W) v8 Z“要不要看一下核磁共振成像?”7 k* d" I6 S2 F
7 t" E2 H2 O+ d# X [* ?/ k1 t
“好的。”
8 V/ X: M5 \1 D% A k. x' O, K8 w" l1 B1 @! S. F
我从床边的电脑上调出来核磁共振图像,指出鼻子眼睛耳朵的位置来引导她,之后我把图像滚动到肿瘤部位,黑色的坏死核被一圈白色肿块环绕着。1 r6 z, R4 W4 h6 f' X) Q& E6 C
/ g1 U9 c0 M; w2 P% n! h6 v“那是什么?”她问道。
& }6 s5 m, `; i7 M9 ]" s) U
3 \% c" B! d& p都有可能。可能是感染。只有手术后才能知道。. b: G* t$ J( A) Z
3 {/ P' s- D( [) o. Y6 i" O
回避问题的倾向仍然坚持着,让他们显而易见的忧虑保持漂浮,不要一锤定音。
" n" [" t+ p/ s" ^; L" ]
# I6 f) R4 v# Q7 K, P0 A6 ?“手术之前我们无从确认,”我说到,“看上去非常像一个脑瘤。”
0 k! F, ^- J5 t) \% k0 }2 U& @3 l: t8 X
“是脑癌么?”+ e) n' b. ^- H Y! X0 u* C
# k: ^ M, q4 |2 m7 |; p7 |1 @7 o
“还是那句话,要等摘除之后,病理师化验了我们才能确切知道,但是,非让我猜的话,我会说是的。”
W; d ^+ M; w3 m/ S# [* y
3 t8 Y/ C0 ?; [0 t% [基于扫描成像,我脑海中毫无疑问认定那是一个神经胶质瘤——一种极其残暴的脑癌,最坏的那种。然而我轻轻的缓慢推进,从李太太和她丈夫那里取得线索。已然介绍了脑癌的可能,我问他们能不能回忆起其他别的事情。坏消息只能是一大锅苦药,需要一勺一勺分发。很少有人要求一下来个痛快,大部分人都需要时间消化。她们没有问及预后——这不像是创伤科,那里你只有十分钟时间来解释,并做出重大决定,在这儿我可以慢慢来。我具体讨论了接下来几天的预期安排:手术的关联;我们只会剃掉一小绺头发,妆容仍然好看;术后手臂会感觉有些无力,但是之后会重新强壮起来;一切顺利的话,三天后即可出院;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休息好非常重要;以及我并不指望他们能完全记住我刚说的所有内容,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讲一遍。: W6 N9 S; P% E( d. n# ~& w( q* r
/ j0 I' Y- b2 h, d8 M
手术之后,我们又谈了一次,这次讨论的是化疗,放疗和预后,到了这时,我已经了解了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具体数据是给研究室用的,不是在病房用的。标准统计,卡普兰-迈耶曲线,衡量着病人一定时间内的生存数字。那是用来度量疾病进展,衡量疾病凶残程度的评测工具。对于神经胶质瘤,曲线陡峭下降到大概只有约百分之五的病人可以活过两年。其次,精确固然重要,可总是该为希望留下一些空间。我不会说“中期存活率是十一个月”或者“百分之九十五的几率你会在两年之内死亡,”,我会说,“大部分病人存活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诚实的描述。问题是,你判断不出来一个个体病人,究竟会落在曲线上的哪个点位:她会在六个月还是六十个月之内死亡?我逐渐相信,超出能力所及的精确程度之外的准确,是不负责任的。对于那些给出具体数字的不足为训的医生(“医生告诉我还有六个月可活‘’),我在想,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的统计学到底是谁教的?
+ c# V, \8 B( P& W6 x# ]" x- }5 ~5 {# b% K, h5 w; O
患者们,听到消息时,大多一言不发。(患者一词的早期涵义之一,就是“忍受困难而不抱怨的人”)不管是出于自尊,还是出于震惊,沉默总是笼罩着。因此,握住病人的手成为沟通的模式。有的人会马上放出豪言(通常会是患者配偶而非患者本人):“大夫,我们会战斗到底打败这玩意儿。”武器不尽相同,从祷告到财富到草药到干细胞。对我来说,这硬气话总是经不起推敲,是唯一能用来击碎绝望,不现实的乐观主义表达。很多个案例,手术迫在眉睫,那种战斗状态很契合。手术室内,灰败腐烂的肿瘤,对于大脑新鲜的桃子状脑回像是入侵者,我感觉到真切的愤怒(逮到你了,王八蛋!我嘟囔着)。摘除肿瘤让人满足——尽管我知道微观下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看上去仍然健康的脑组织。几乎不可避免的复发,那会是另外一天的问题。一次一勺,徐而图之。对于人的联接的开诚布公,并不意味在后殿就揭露弘大的真相,而是和病人在他们身处的位置相见,无论是前厅还是中殿,尽可能带他们走的更远。
3 ~7 ~0 A2 j' } ^: R& M2 n8 s4 a% P7 s8 r+ n( L. A, v
然而对于人的联接的开放也要付出代价。
& j# ~0 D. | j& F( v4 _% Q
% ?5 n+ |5 z m, }住院医第三年的一天晚上,我碰到翟复,普外科的朋友——普外也是差不多的紧张和艰苦。我俩都注意到了对方的消沉。“你先说,”他说。我描述了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穿了颜色不对的鞋子被一枪打在头上,可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能抢救过来……在近来一堆致命却不能手术的脑癌患者中间,我寄希望于这个孩子能救回来,却回天乏术。翟复停在那里,我还在等着他的故事。反之,他笑了,猛拍了我胳膊一下说,“好吧,我算是明白了:只要我感觉自己工作低落,就找个神经外科医生,总能把自己聊开心。”, k0 G% i" h1 Y3 U- Y
0 B+ \6 T3 b V8 M( c那天晚上,在温柔地给一个妈妈解释了她的新生儿生来没有大脑,将不久于人世之后,我开车回家,打开了收音机。全美公共台NPR正在报导加州的持续干旱。突然之间,我泪流满面。 x) P8 Y) B( c9 M
( B5 G6 W$ y0 _3 A; u
这些时刻与病人同在肯定会付出情感代价,然而也有回报。我从没有哪怕一分一秒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的问题。保护生命——不仅仅是他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身份——的召唤,神圣自在。3 L+ M! ?. s( |2 f, _
0 {& D: P' C6 O9 [我意识到,在患者大脑上实施手术之前,我必须首先理解他的意识:他的身份,他的价值观,他觉得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还有什么样的损伤,会使得任其生命终结变得合理。我戮力前行的代价很高昂,难以避免的失败给我带来几乎无法承受的内疚。那些负担恰好让医学充满神圣,却又全不可能:背负起他人的十字架,有时候你会被那重量压垮。 |
|
|
|
|
|
|

尚未签到
住院医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会有专门辟出的时间来进行额外的培训。这可能是医学领域独有的,神经外科的职业理念——全面卓越——单纯保持神经外科领域的卓越还不够。为了在该领域执业,神经外科医师必须前进探索,在所有其他领域也要全面超越。有时候这些其他领域很公开,就像神经外科医师兼记者桑吉·古普塔的情况,但是更常见的是,医生会专注于相关的领域。最残酷最荣耀的路径,是成为神经外科医师兼神经科学家。+ K! M8 P( x* d! _
$ F: Y" I2 F, v2 \! _+ o0 }( I$ A第四年,我开始在斯坦福的一个特殊实验室工作,那个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基本驱动神经科学,以及开发神经假体科技——使得,比如瘫痪的人可以通过精神来控制计算机光标或者机械手臂。实验室的头儿,一位电子工程兼神经生物学家,同是二代裔,被大家亲切的叫做“威V”。威比我年长七岁,而我们处的像是兄弟。他的实验室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阅读大脑信号的领导者,但是有了他的支持,我得以开始着手一个与之相反的项目:把信号写入大脑,也称为“神经调制”,然而所及范围不仅限于此:能够控制神经发射,潜在上既可治疗一系列当下不能治疗或难以治疗的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疾病,从重度抑郁症到亨廷顿舞蹈症,到精神分裂症,到妥瑞症(儿童秽语多动症)到强迫症……无限可能。而今把外科手术放在一边,我开始着手学习,将基因疗法的最新技术应用于一些列的“首创性”实验。3 ~4 D! x& x) {; |& k" r
& i' n3 L2 t9 h% ]0 Q
一年之后,有一天我和威坐下来进行例行的周会。我已经喜欢上了这种讨论。威不同于我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他轻声细语,对人和临床任务有着深深的关切,威常跟我坦言,希望他自己也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科学,我逐渐了解到,和你会从事的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充满着激烈的政治和竞争,充满着寻找捷径的诱惑。
/ D- {" `1 Y0 {8 Z/ _9 A$ p1 K* x/ W% _, M0 H
威永远令人放心地选择诚实的(并且通常是谦和低调的)前进之路。尽管大部分科学家都合谋,寻求在最著名的期刊上发表成果,并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威让我们保持的唯一规矩,就是忠实于科学自身,并且不折不扣如实陈述。我从未见过如此成功,却又如此坚持正道的人,威实在是堪称典范。
# @2 R0 P0 p. a) J. b7 |
3 } b7 {7 `) m1 [# X3 t8 k我在威对面坐下来,他没有笑,看上去很痛苦。叹了口气,他说,“现在我需要你扮回医生的角色。”1 {2 @5 W" A5 z- _6 O, `
5 j, C6 \: J3 Q/ W5 [“好啊。”* }8 I! n+ _/ B* \% `
8 [5 J; |( _$ w5 |0 D1 B" k- \“他们告诉我,我得了胰腺癌。”
; G3 N7 B* `. [2 ^5 X
5 V' p/ r7 V& N& \; h A$ H4 v H“威——好吧。跟我说说。”. O: V( E, c$ m) N I0 a
# H& p7 k' L8 a5 l. G h9 U' U! E
他摆出了自己的体重降低,消化不良,还有近来做的“预防性”CT扫描显示胰腺上面有阴影——这个阶段确实非常规的检查。我们讨论了前面的路,还有近期要做的可怕的惠普尔手术(“你会感觉像被卡车撞了一样,”我告诉他),最好的外科医生都有哪些,疾病会给他的妻子孩子带来的影响,以及在他长期缺席的时候实验室如何运转。胰腺癌预后凄惨,但是当然没办法知道那对于威而言,意味着什么。
8 @7 L( [, j9 b3 l% h ]8 Y
* d2 D% p: k: f+ R威停顿了一会儿。“珀奥,”他说,“你觉得我的生命有意义么?我做的选择对么?”
, z$ w& ]! r' U$ F6 @# D1 Q/ A5 {+ Z: U5 U
这让人瞠目结舌:就连我视为道德楷模的人,在面对自身的死亡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8 f& a9 E* [( i+ r5 A) j4 s" j; N+ O9 [1 h9 I
威的手术、化疗和放疗是探索性的,但是成功了。一年之后他重返岗位,当时我正马上要返回医院的临床工作。他的头发稀疏花白,眼睛里的火花黯淡了。我们最后一次的周会,他转向我说,“知道么,今天是我头一次感觉全都值得了。我的意思是,很显然,为了孩子们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今天是第一天,似乎所有的苦难都值得了。”
. k4 ~: t8 d& i0 {$ R+ U4 t5 G- I6 X; s8 l: k1 }+ G$ V
医生对于将病人穿过的地狱了解的是多么的少啊。 |
|
|
|
|
|
|